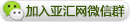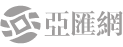孩子上五年级时,周晓燕一度觉得家里“鸡飞狗跳”。两人因为手机问题争吵,女儿“砰”地一声把房门摔上;周晓燕说话语气严厉些,女儿就嚎啕大哭。
这样的情形持续了一年多,周晓燕理解为“青春期逆反”。直到有一天,女儿主动和她说:“妈妈你带我上医院吧。我感觉对任何事都不感兴趣,老想睡觉。”在孩子再三要求下,周晓燕带她去了三甲医院,医生开出的诊断是重度抑郁。
周晓燕一下子呆住了,“好好的女儿,怎么突然就抑郁了?”但她又感到手足无措:“如果是我的问题,我改。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和她说话,害怕伤害到她。”
近年来,青少年抑郁受到社会各界关注。2024年5月发布的《2024儿童青少年抑郁治疗与康复痛点调研报告》显示,被诊断为情绪障碍的儿童青少年,首次确诊的平均年龄为13.41岁。今年4月,《心理健康蓝皮书: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3-2024)》发布,其中的《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现状及康复困境研究》显示,只有不足三成的家长会在孩子首次主动寻求专业帮助的情况下带其就诊。家属缺乏心理健康常识以及不知如何求助,是排名前两位的延误原因。
如何识别孩子抑郁症的早期“求救”信号?当孩子抑郁了,家长如何成为“坚实后盾”?
“不爱上学”只是一种征兆
程小棋是在女儿小恩主动说“妈妈我想去看心理医生”时,才发现“不爱上学”只是一种征兆。
初一上学期,小恩开始频繁地说“妈妈我不要去上学”,但程小棋觉得“应该还能坚持”。直到有一天,程小棋接到了语文老师打来的电话,说小恩在日记里写下了“自杀倒计时”,意识到问题变得严重了。
课程难跟上,作业做不完;中午吃完饭后,老师有时会让没有写完作业的学生站起来,小恩常常是少数几个站起来的学生之一;分组学习时,小恩觉得自己是小组里拖后腿的那个,“整个人都非常糟糕”。
除了学习,还有社交困扰。原本关系很好的女生朋友突然“断崖式绝交”,小恩试图见面问清楚,对方也不见。这让小恩在学校有一种“被遗弃感”。
慢慢地,在初一入学时说“妈妈我好喜欢这个学校”的她渐渐不爱说话,一靠近学校就哭,老师点名会不自觉地发抖,在严肃场合控制不住地嗜睡。初一下学期,经过专业医生诊断,小恩出现了中度强迫和中度抑郁。
程小棋最初感到十分无助和迷茫,“从来没觉得孩子会发生这些状况”。
“我一直觉得自己做得还不错。没有‘卷孩子’,相对比较理解她,任何合理需求我都会尽量满足。工作不忙的时候都会陪伴她、带她出去玩。我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问题了。”程小棋说。
在北京安定医院儿童精神科医生曲天宇的门诊,很多是六年级到初三的孩子,孩子向家长至少求助3次,家长才会带孩子来就诊。
曲天宇发现,因抑郁症前来就诊的孩子有几个共同特点,最常见的就是厌学,还有的是因为身体不舒服、和同学关系不好。但家长在早期往往不重视,以为是叛逆期到了,或者单纯不想学习。直到孩子出现功能上的退化,比如实在无法上学,有的甚至严重到伤害自己、产生轻生念头。这才被送来就诊。
如何识别孩子抑郁症的早期“求救”信号?
曲天宇表示,从诊断来看,抑郁症的孩子通常有一些核心症状。在情绪上,除了常见的情绪低落、高兴不起来、感到绝望和无价值之外,易怒和暴躁在青少年中也很常见。其次,这类孩子的躯体不适症状会格外严重,比如不明原因的头疼、胃疼、失眠、食欲不好、体重下降等,有一些孩子可能也会呈现嗜睡、白天困倦。行为上可能出现自伤,容易有冲动言行,有的孩子会回避社交、不去学校。
“值得注意的是,孩子的暴躁冲动、手机过度使用也需要关注,家长不能简单归结于青春期叛逆对抗和网络成瘾,事实可能远不止如此。”曲天宇表示,当出现上述核心症状两周以上,同时孩子的社交、上学等社会功能受到了影响,家长需要及时关注,必要时带孩子就诊。此外,在情绪好转后,孩子可能依旧存在注意力不好、记忆力下降,成绩持续下滑、人际关系不良等症状,也需要持续的关注和处置。这是一个全病程管理的过程。
曲天宇提醒,家长也不要过度紧张。抑郁症的诊断需要从症状的严重程度、持续时间和对社会功能的影响等多方面进行评估。诊断和治疗不要自行对号入座,需咨询专业医生。
父母要稳定自己的内核
今年21岁的陈安,第一次确诊是在5年前读高一时。从初中到高中,课业压力剧增,陈安觉得自己的情绪越来越低落,每天都很累,被什么东西压着,连起床都要用尽全力。有时候会突然哭出来,觉得“活着好难”。
可当她试着和父母说这些时,他们却觉得只是“想太多”。陈安向心理老师求助,后在医院诊断出中度抑郁。当陈安告诉爸妈“我好像抑郁了”,妈妈的第一反应是“年纪轻轻瞎想什么,手机玩太多了”。爸爸则说:“多出去走走就好了,别这么矫情。”
“他们的话让我更难受,好像我的痛苦根本不值得被认真对待。”陈安说。
曲天宇观察到,门诊中许多家长都会谈“抑”色变。当医生和家长说孩子抑郁的情况,家长的表情和状态会发生明显变化。可能从一个安静地和你陈述的状态,变成拍案而起:“凭什么说我家孩子抑郁了!”
“我的孩子是不是被别的抑郁症孩子带的,被传染了”“都是和别人学的,别的孩子不上学,他也不想上”……曲天宇发现,很多家长会否认孩子生病,认为“家丑不可外扬”。
在病耻感的“加持”下,这些家长往往对治疗也存在很大的抵触情绪。曲天宇举例,有的家长认为药物会损伤孩子的大脑发育,只要规律作息和运动就能解决问题。有的家长则绝对信任医生,吃了医生开的药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孩子吃完一袋药,发现还是不能上学,社会功能持续无法恢复,回来说你这药不对。”
广东白云学院应用心理学系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学院教育博士(在读)陈晓也遇到过这类家长,在孩子抑郁后说“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呢,你不要那么矫情”。
“每一代孩子所处的社会现状或生活方式都是不同的,父母不要用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感受看法去替代孩子的体验。”陈晓发现,对于很多困在抑郁症里的孩子而言,很痛苦的一个点在于,连家长也无法理解自己为什么这么痛苦。甚至有的家长对孩子还存在抱怨和责怪,觉得“别人比你还惨都没抑郁”“你怎么弄出这么多麻烦事”。
另一类家长则陷入“都是我的错”的泥淖,否认自我,无法正视孩子的疾病。
“这些家长会把教育模式完全颠覆,与孩子相处变得小心翼翼。但这样反而给孩子传递出担忧、紧张、恐惧等情绪。家长如果心态也不稳,家庭就会变成暴风雨中飘摇的小船,对孩子的治疗和恢复无益。”陈晓说。
没有“完美父母”
为了帮助女儿,程小棋作过一系列尝试。起初,她基本把工作放下了,在家陪着小恩,去医院做检查。“那时她不想上学就不上学,可以在家休息,不想做作业,我就跟老师说。我没有逼迫她,可以上学了我们就试两天,不行又回来。”
小恩做了很多检查,发现没有生理上的问题。尝试了很多方法,小恩依旧不能回去上学,程小棋有一些愤怒。“我就觉得这有什么难的吗?现在学校的生活水平比我们那个时候好多了。”
最初程小棋尝试和女儿讲道理,讲人生遇到一些挫折是难免的,小恩觉得妈妈说得有道理,会硬着头皮上学,回来后发现还是不行。小恩在学校会主动向老师求助,但这份袒露带来的是额外的关注度,比如经常被要求做心理测评,无形之中也给小恩带来了更多心理压力。
关于上学的拉扯持续了快一年。最初是一两天,休整好了再回去,之后是一两周,到初二上学期可能连续三四周都去不了。在又一次把小恩送到学校大门口,小恩崩溃大哭时,程小棋当下给老师发了个消息,说今天不来了。
“我累了,我不想再跟孩子老师谈这个事情,也不想一直被叫到学校。”程小棋说,“回家后我又和小恩确认了一遍,是不是实在挺不住不想上了,她说是的,于是我们决定停学。”
那一刻之后,家里恢复了平静。有时候程小棋也会试图寻找女儿抑郁的原因:是不是因为我没有陪伴她,是不是因为原生家庭……在很多个不眠夜,程小棋刷到专家直播间,会忍不住去想这些问题。她的朋友劝她,不要深究这些原因,不要太过自责。
“许多网络上的所谓科普说,孩子的问题都是家长的问题,这其实是加重家长的焦虑。”陈晓指出,这些指责若没有建设性意见,只会激化矛盾,提供不了社会支持。家长如果听了这些视频的言论,一旦孩子出什么问题,就会立刻反思自己是不是哪里做得不好,开始感到内疚。内疚过后,转变了养育方式,以为转变孩子的学习方法就能让孩子康复,如果孩子没好,就会变得更加愤怒,陷入失控的情绪,让局面变成死循环。“抑郁症孩子的家长已经很艰难了,不要再去加重家长的负担。”
“没有完美的父母。”陈晓表示,父母本身也是普通人,肯定会犯错,当然,这不能成为父母伤害孩子的理由,但同时,也不应该把所有矛头都指向父母。应当正视心理疾病,而不是异化它。
如何陪孩子打赢“持久战”
“为什么我做了这么多努力,孩子还是没有好转?”这一度让李莹焦虑。
李莹的儿子读初一,一年前确诊抑郁。李莹过去经常出差,得知孩子抑郁后,她辞掉了工作。“我心里想着,过去给儿子的陪伴太少了,我想陪他度过这段艰难的日子。”
刚开始,李莹以为,只要时刻守在孩子身旁,把关心做到极致,他就能渐渐康复。但事情远没那么简单。精心搭配的饭菜,儿子常常只是敷衍吃上几口;李莹满心期待地提议出去走走,儿子却满脸不耐烦地一口回绝;想和他好好谈谈心,他却把自己锁在房间,怎么敲门都不回应。
李莹问他:“宝贝,妈妈为了你连工作都不要了,你怎么就不明白妈妈的苦心呢?”儿子却哭着喊:“你根本就不懂我!你觉得这样围着我转,我就能好起来吗?你从没问过我是不是连呼吸都觉得累!”那一刻,李莹的心像是被重锤猛击,委屈、无奈一下子全涌了上来。
陈晓指出,家长首先需要对抑郁症有正确的认知,了解康复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对孩子有更多耐心。有的家长发现孩子生病了,会改变自己的关心方式,如果过了一段时间孩子还没好,就会很愤怒:“我都已经做了这么多了,为什么还没好?”
曲天宇表示,家长首先应当正确认识和接纳孩子的疾病。有的家长存在一些误区,认为只要能给孩子更多的陪伴和支持,孩子就一定能好起来。但抑郁症的治疗是一场持久战,过多的付出往往对应着过高的期待,当家长发现孩子心情好一些仍然不能上学时,会使他们对于康复的信心降低,甚至产生放弃给孩子治疗的想法。“如果真的不知道如何给予孩子适当的帮助和支持,可以向医生求助。”曲天宇说。
“家长需要首先接受:我的孩子生病了,恢复可能要花很长的时间。”陈晓说,他见过有的家长,虽然口头说“我接受孩子这样”,实际上还是变着各种法子尝试去改变孩子。
陈晓建议,家长首先需要稳住自己的心态。如果过分焦虑,可以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把自己的情绪和状态调整好。其次,可以考虑以家庭为形式的心理咨询,与孩子一起接受专业心理咨询师的帮助。此外,可以配合正念等形式,对自己的情绪有觉察,稳定内核,才能给孩子提供额外的辅助和支持。
除了认清和接纳孩子的疾病,家长要避免说一些话,如“你想太多了”“别人都没抑郁,你咋抑郁了”,应该理解和接纳。曲天宇说:“或许家长不一定完全理解孩子为什么这样,但至少可以对孩子表达,我知道你现在很痛苦,我们一起去面对这件事,去寻求专业医生给的专业意见。”
此外,对于抑郁症青少年发脾气、暴躁等情况,有的家长完全不能接受。“我们得允许孩子发脾气或者哭泣,冲动的自伤或伤人行为除外。”曲天宇表示,如果是简单的情绪发泄,比如哭泣、捶打枕头等,家长不用立刻打断他,也不要直接抱住他说不能这样。要允许他拥有发泄的空间。
家长可以每天抽出15分钟到半小时陪伴孩子,哪怕只做一些简单的小事,如散步、看剧、一起做晚饭。“不用反复和孩子谈到疾病,只要明确诊断,确定治疗方案再践行就好。作为医生,我们更希望家长在保证孩子安全的同时,做到医嘱的谨慎执行和病情观察,而不是在孩子还处在痛苦之中的时候成为他们的‘心理治疗师’。”曲天宇建议,当孩子症状有好转时,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运动,有助于刺激快乐情绪的释放。
手机使用问题需要格外重视。“急性期待在家的孩子,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作息没有规律,手机不离手。”这需要家长学习运用一些行为管理的技巧,在家里重新构建规律的作息,成为对孩子手机使用和基本行为问题的管理者,协助孩子在家里养成好习惯,逐渐回归学校和社会。
小恩生病后,程小棋并没有把这件事当作是“生活要塌了”,想出去玩时,程小棋就会带着小恩出门,去吃好吃的,还去泰国清迈旅居了一个多月。
在程小棋把自己和小恩的经历分享到短视频平台后,评论里会出现一些指责:“你完全不理解你的孩子,一个得了抑郁症的孩子根本就不想出门,你却用你的方式非要让她融入。”“你真是个强势的妈妈。”
程小棋认为,一个孩子生病了,如果不管他,让他自己待在家里,会把痛苦放大到极致。“其实很多人对抑郁症还是有误解,认为生病了什么都不能干。不要让孩子沉浸在里面,可以换个环境转移一下注意力。有的孩子渴望被带出去,但父母不知道该怎么做。”
不上学的时间里,小恩会画画,和一个澳大利亚女孩成为“外语搭子”,还在青少年社区和不同年龄的孩子一起交流,情绪上有了改善。
在自媒体账号的后台,很多人会和程小棋发私信倾诉。令程小棋印象深刻的是,有一个读者写自己小时候也因为心理困扰无法上学,但很幸运有一个非常爱自己的妈妈,允许自己不上学。“有一天他的妈妈说,想吃一个瑞士卷,这个孩子尝试去学烘焙,后来发现自己非常喜欢烘焙,获得了内心的平静,还能用这个方式谋生。”
“他对我说,希望我和小恩之间,未来也会有一个类似‘瑞士卷’的灵感瞬间。”程小棋说。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除陈晓、曲天宇外,其余为化名)